在爱荷华大学研究生院第一年的下半学期,我选修了一门关于《白鲸》(Moby-Dick)这本小说的课。在那之前,我已经完成了本科学业,而且大学毕业后的几年中有一段时间是为杂志写美国小说评论。不过,我从未完整读过这本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杰作——它通常被称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我读了很多关于《白鲸》的介绍和评论,这些评论给我的收获就是知道了我其实从未读过这本书。我的写作经历也让我知道我应该读这本书。现在,我需要更多的背景,我也需要有人督促我去读这本书,我希望选修这门课程能够迫使我在这方面下点苦功夫。
不过,比起这本著作本身,更吸引我的是教授这门课的老师。这门课由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教导,她是《管家》(Housekeeping)和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基列家书》(Gilead)的作者。罗宾逊的作品熏陶和指导过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从约翰·派博(John Piper)到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她的文字平实而抒情,思想坚韧而宽广,立足于今生却向永恒敞开。
她的作品优雅而奇特,常常摒弃章节的划分和通常的情节进展方式,像祷告一样蜿蜒地走向启示。这些作品不像是小说,更像智慧文学;不像文学,而是思想本身。
罗宾逊在美国文学界算是一个相当“老顽固”的人物。还有哪位21世纪作家会像她在《基列家书》中所做的那样,专注于描写一个垂死的、对棒球、废奴主义和乔治·赫伯特的诗情有独钟的牧师?还有哪个作家能把善良和美德写得如此有趣?罗宾逊的这种写作风格来自哪里?我很想知道,《白鲸》对她意味着什么?
我有一个这样的猜测:《管家》的第一句话(“我叫露丝”)与《白鲸》的第一句话(“叫我以实马利”)是一种呼应。我认为,这两本书都是通过一个高度反思性人物的离散思考看待现实,这个人物既是独特的,又能代表人类的认知。这两本书都运用了隐喻来探索存在的本质,并且对认知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质疑。
可以说我在2013年秋天注册这门课程时,我感到兴奋,也有点紧张。但当我在寒冷的第二个学期第一天进入教室时,我的期待已经被一种惧怕所取代。寒假期间,我从华盛顿州调到爱荷华市开始的编辑工作在没有任何提醒的情况下结束了。我妻子的自由写作收入和我因教授本科写作课程而获得的津贴,对一个四口之家来说并不足够,更不用说我们即将成为一个五口之家了。
长期以来,“写作决定出路”一直是我的口头禅,但现在我已经很难在纸上写出句子了。我已经开始怀疑当初离开华盛顿的决定(我在那里从事了将近十年的新闻工作,我们计划在完成我的文学硕士学位后再搬回到那里)是否不明智?我是否错误地把对文学梦想的顽固追求当成了一个可敬的支点?
突然间,与罗宾逊一起读《白鲸》的前景感觉像是一种奢侈,现在我没有理由放纵自己去享受这种奢侈。当你都不知道该怎么买菜的时候,怎能沉浸在伟大的名著中呢?更不用说写作了。
这种焦虑,无论听起来多么合理,都显示出更深层次的不信。在内心深处,我在质疑神的护理——“质疑”不如说是指责。我的基督信仰自从14岁时一个传道人与我分享福音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却充满了臆想。是我让环境蒙蔽了我对现实的看法。老话说的没错,钻石的确需要好好擦拭。虽然有很多事情帮助了我,但却是《白鲸》选修课帮助我设定了正确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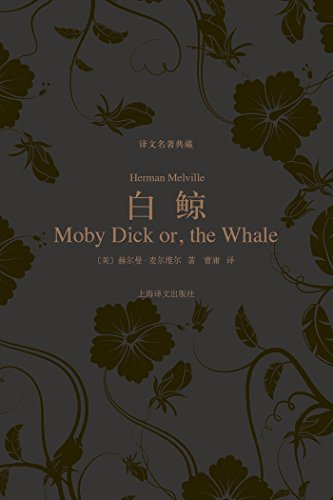 这门课在周三下午举行,地点是弗兰克·康罗伊阅览室(Frank Conroy Reading Room),这是一座庄严的维多利亚式老建筑,也是“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所在地。阅览室里一边是高大的窗户,俯瞰着冰封的爱荷华河;另一边的玻璃书架上则陈列着校友们的作品,包括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华勒斯·史达格纳(Wallace Stegner)、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安东尼·马拉(Anthony Marra)、李翊云(Yiyun Li)等等。选修了这门课程的学生包括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和翻译家,他们来自本校的研究生写作项目,还有客座教授和一些附近城镇的旁听生。当罗宾逊走上讲台时,我几乎听到了所有人的凝重呼吸。
这门课在周三下午举行,地点是弗兰克·康罗伊阅览室(Frank Conroy Reading Room),这是一座庄严的维多利亚式老建筑,也是“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所在地。阅览室里一边是高大的窗户,俯瞰着冰封的爱荷华河;另一边的玻璃书架上则陈列着校友们的作品,包括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华勒斯·史达格纳(Wallace Stegner)、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安东尼·马拉(Anthony Marra)、李翊云(Yiyun Li)等等。选修了这门课程的学生包括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和翻译家,他们来自本校的研究生写作项目,还有客座教授和一些附近城镇的旁听生。当罗宾逊走上讲台时,我几乎听到了所有人的凝重呼吸。
罗宾逊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有一种复杂的平民气息。他们的深刻性,以及这思想固有的给人带去惊讶的能力从未受到过质疑,但却能够以平实的语言转达出来。他们的思想和嘴巴之间好像有一个隐含的分别,默认舌头只是人类意识这一无底泉源的井口。在这方面,福克纳(Faulkner)似乎有很多影响。
然而在课堂上,罗宾逊的智慧得到了充分展示。她说话总是用长长的、鼓舞人心的句子,这些句子的转折和流向精炼且不可预测。她引用了丁道尔和当天《泰晤士报》的文章。她诵读了约拿书的经文,引用了奥古斯丁、狄更生、海森堡、洛克,她对宇宙学、现象学、历史和语言学也很有研究。作为一名受过速记训练的记者,我尽可能地在我两岁女儿用橙色蜡笔涂抹过的黑色8.5 x 11英寸Moleskine本子上进行速记,希望以后能重新审视这些笔记。但另一方面,罗宾逊却很少查阅自己的稿子。
我该如何描述她的声音呢?可以说是淡淡的、没有烦恼的。她没有向听众推销任何东西,配戴着一个领夹式麦克风,每次她的银色头发落在上面时,麦克风的声音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她会把头发撩上去,这时她的声音会有一个变化,让你觉得好像自己也在帮忙一样。事实上,这是我对这门课的一个持久印象,一种讲台带来的引力,并透过讲台进入罗宾逊思想的宇宙。
《白鲸》是一部出乎意料的小说,既吸引群众,又离经叛道,既深刻又广泛。它既是一本散文集,又是一本参考书,是圣经中的寓言,是莎士比亚式的独白,是滚滚的海洋叙事,是一首散文诗。支撑这本书的是梅尔维尔笔下滔滔不绝的叙述者以实马利——一位来自曼哈顿的流浪水手,他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港口加入了“裴廓德号”("Pequod")成为船员,这是一艘由狂热分子亚哈船长驾驶的捕鲸船。
对亚哈来说,白鲸如同一个愤怒的、反复无常的神。《约伯记》中对此也有令人难忘的描述。“你能用倒钩枪扎满它的皮,能用鱼叉叉满它的头吗?”上帝在该书的最后几章中这样论及利维坦(和合本译作“鳄鱼”——译注),“你按手在它身上,想与它争战,就不再这样行吧!”
亚哈对此的回答是:“哦,是吗?愿意打个赌吗?”他已经被鲸鱼吃掉了一条腿。
船长具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式冲动,他拒绝接受人们通常用的那种尝试性努力,这预示了这艘船的命运。然而,正如唯一的幸存者以实马利叙述的那样,裴廓德号的不守常规带来了真正的超越,因为船员们——包括黑人、美洲原住民、贵格会教徒和异教徒——在鲸鲨海兽出没的大海上找到了一种团结一致的友爱。
在每一个主题上,罗宾逊都有发言权。她说,像惠特曼和林肯一样,梅尔维尔培养了一种包容美学,与19世纪在欧洲扎根并在20世纪将其撕裂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一致。是良知——而不是遗传、母语或历史——将个人联合起来,并赋予他们在这个新世界的价值。她说:“《白鲸》站在欧洲哲学传统之外的事实,不一定是一种对它的批评。”
罗宾逊这种对理解梅尔维尔的理解基于19世纪的新英格兰宗教文化,她坦率地说,自从一位大学教授指派她写了一篇关于清教徒的论文以来,她就一直对这种文化保持兴趣。对此,她解释说:“我确实喜欢阅读前现代著作,那时的人对死亡有更多的认识。他们看到了太多的疾病、死亡和痛苦,才会对公平的问题感到困惑。对他们来说,这问题显而易见,就像对《约伯记》的作者一样,世界是由一个不同的、更神秘的法律所支配的。”
在课上,我们读了来自爱德华兹和加尔文著作的摘录,这两位神学家关于人类尊严和堕落的观点,以及神的旨意和人类责任之间的相互作用,支撑着梅尔维尔的形而上探索。她说:“恐怖和欢乐、甜蜜和可怕、苦难和荣耀……在基督教传统中,这些东西是一起呈现的,而且并非彼此否定,也不是彼此竞争,而是有关系的,有乐趣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同一经历的两面。”
罗宾逊很喜欢《白鲸》。她的平装本看起来像一个臃肿的抽屉,已经皱得无法修复了。每隔一页都有标记。她读过无数次这本小说,也反复地把它当作过一种教导资源,但她仍然陶醉其中。她会长篇大段地朗诵其中的文字,有时会自嘲,有时徘徊在某些短语的转折处,就像投入了一种私人的热情。在朗诵了“狮身人头怪物”一章中的这句话——“一片铿锵有声似的宁静,像一棵黄色的大忘忧树,正在把它那无声无息又不可数计的树叶,越来越多地铺开在海面上。”——之后,她叹了口气,说:“我们能说什么?他有一种天赋。”这就是阅读《白鲸》的方式:慢慢地,充满期待地,带着乐趣,带着感恩。
罗宾逊说,像所有其他伟大的作家一样,梅尔维尔关注的是知识问题。他的指导性问题是:“你如何从压倒性的、不透明的事物中获取对人类有意义的东西?”她声称,作者对捕鲸者、捕鲸传说和捕鲸贸易中的体力劳动进行了乏味的、甚至是带着强迫性的描写,这与《圣经》中的现实主义概念有关,这种全面的世界观坚持宇宙的不可捉摸性和每个人生命的意义同时成立。罗宾逊说:“在加尔文主义中,对你的最大要求是关注——关注神、关注他人、关注自己。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值得沉思的主题。”
这一说法打击了我,但同时也给了我一个重新定位的思考。我一直在关注什么?不是对神,而是对不如意的抱怨;不是对他人,而是对恐惧。我没有在我的经历中寻找智慧,没有花时间在祷告中呼求。我怀疑有一种意识主动地在这个世界上做工,更不用说在我的生活中做工了。我一直在觊觎其他的经验——更清晰、更少不舒服的经验。
在一对一的访谈中,罗宾逊告诉我,她一直在阅读威克里夫的信件,她被他所强调的为自己所做不该做的事情悔改,以及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为自己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悔改所感动。失败和恐惧一样,都有其用处。她说:“世界给我们的恐惧是我们发现自己的地方,因为世界给我们的恐惧也是我们背叛自己的地方。”
在“喷泉”这一章中,本书对鲸类喷水孔做出了具体的描写。以实马利将海洋中央喷出的雾气这一令人不安的景象变成了光照的隐喻。他说:“在我脑里的种种迷云疑团中,总不时地有直觉的神力显现出来,以一种圣光来点破我的迷津。”
当我每周认真聆听罗宾逊的讲课时,我也在雾中瞥见了一束光。即便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被蜡笔涂抹过的课堂笔记,我也能感觉到古老真理正在破晓的快感。我并不是完全掌握了失去工作的意义,也不是说我有任何保证好像事情会按照我的计划进行。而是罗宾逊为我确认了,期待意义是多么正确、多么意义,以及期待对信仰生活是多么重要。
教师所做的比教书更多,所教的比他们以为的更多。罗宾逊对加尔文的评论让我重新翻开《基督教要义》这一套两卷的书。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一位牧师朋友送给我的。罗宾逊对爱德华兹的思考让我想起了我在大学二年级时读过的讲章,那时我第一次开始对上帝的荣耀、我的顽固和基督的赎罪之爱有了概念。这两位神学家推动我回到圣经中,我在对现在的抱怨和对未来的担忧中一直忽视了圣经。写作的速度很慢,但现在写作的渴望又回来了,写作的热情也会随之而来。
在课堂的最后几分钟里,罗宾逊让大家提问。学生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她是如何看待霍桑的,梅尔维尔声称《白鲸》是为他而写。罗宾逊说:“我希望我能够公平对待霍桑,但他的作品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有一次,一个学生问罗宾逊是否相信有外星人。“我认为我们肯定是唯一的人类,”她回答说,“但即使另有一个智慧生命,那也会是两种‘人’,这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在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我们都在想的问题:现在还有可能写下像《白鲸》这样的作品吗?罗宾逊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写一本就知道了。文学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她从讲台后面走了出来,继续说:“我不是在谈论自我欺骗。我说的是那种不需要文化认可的自信和自律。”
教师教的比他们以为的更多。在接下来的几个学期里,我将与其他杰出的作家一起上课。我将找到慷慨的导师、严厉的读者和鼓舞人心的同龄人。我还将参加罗宾逊的两门课程,一门是旧约,一门是新约,但我记得在《白鲸》选修课之后的想法:如果我不得不在没有完成所有课程的情况下离开爱荷华,那也不会是一种浪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一直在等待的东西其实是这个。那是一种责备,同时也是一种许可:关注、接受亮光、写作。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eading Moby-Dick with Marilynne Robinson.